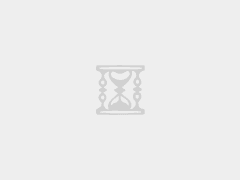A. 徐城北:无心巧遇张火丁(王娜)
《城北说戏1:京剧这玩意儿》 徐城北 著 定价:32.00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《城北说戏2:京剧夜明珠》 徐城北 著 定价:32.00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王娜 编辑
《城北说戏1:京剧这玩意儿》
徐城北的“说戏”是有来头的。自幼跟祖父瞧戏,又出身记者世家,多与梨园名角耳濡目染,虽无心插柳,却又命中注定在专业剧团当编剧搞研究,一干15年。写过剧、论过戏、出过专著,但如同人们称他“城北徐公”,并不因其貌得名一样,他的杂(涉猎广泛)、散(散论闲文)、玩(把玩品味)成就了他的非专业写作,更多了读友。于是一发不可收,越发信手拈来,在若干“三部曲”后,开始“五指连弹”。这不,就有了被他称为私人记忆的5本“说戏”。其实,书中不只说戏,也说人说事儿,这或许正是读者想看到的。
《城北说戏2:京剧夜明珠》
徐城北的“说戏”是有看头的。他居然将京剧与粤剧,张火丁与红线女,谭鑫培和于魁智,袁雪芬、袁世海……都当作“夜明珠”串在了一起,还就此聊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,当然也免不了说一些大剧场和小园子、演员的挣钱与读书等话题,发一些“切忌买椟还珠”,“别了京剧革命”等议论。
跟红线女相比,程派再传弟子张火丁再优秀,也只能算是小号的夜明珠了,但她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
我跟火丁应该算是“同事”,都在中国京剧院“拿银子”(领工资)。但她来得晚,她刚来我就调走了,真正的认识过程很奇怪,就发生在红线女临时借住的地方。那阵我正为粤剧红线女写着书,每周要到她住处谈三个半天,我是在那里“先遇到、后认识”张火丁的。此话怎讲?有一天临近中午,火丁推门进来了。不施脂粉,非常朴素。我与张火丁对视良久,没有言语。红线女问我:“你们认识么?”我摇头。红线女奇怪了:“你们一个剧院,怎么会不认识?”
火丁则试探着问:“是城北老师么?”我被动地点头,问道:“你是?”非常朴素的回答:“我是张火丁。”哦,她当时就很有名气了,我居然不认识台下的她。我仅仅是在台下看过她的戏,这样素面在台下相遇,还真是第一次。估计红线女一定会暗笑。但我脑子飞转:她怎么会到红线女这儿来?没有红线女的召唤,她肯定不敢贸然拜访的。总之,红线女看上她肯定有蹊跷,而她这么年轻就倾倒红线女也绝非寻常。
我继续跟红老师谈她的艺事,张则静静坐在一边,好半天没插一句话。最后我谈完了,转过头问火丁:“你找红老师有事吧?”“没,真的没。就是来看看的。”红也插话:“我一会儿再招呼她……”我很奇怪:远在南国的大明星,会看重远在北方的“小程派”。其中,必然有连火丁也未必明白的道理。
说火丁是“小程派”,一点也没冤枉她。她当时确实还很“小”。当时的“程派大家”基本是三位:赵荣琛、王吟秋、李世济。前两位是给程先生磕头的男学生,后一位是干闺女。前两位最好的时候似已过去,但还能支撑一气。李世济当时有丈夫、儿子辅佐着,谢幕时一家三口都走上舞台中心,这种幸福感不是每个演员都能拥有的。我当时一方面给李写本子,同时又为他们夫妇写文章。我属于程派笔杆子的“第三世界”。这是剧院朋友与我开玩笑,这样说过了还让我别生气。我这人随和,听了无动于衷。因为我“傍”李世济是工作需要,我与她是一个单位(中国京剧院)的,而赵与王都不在我们这里。我不可能完全脱离单位去辅助单位之外的名家。更何况,我这“三个世界”从根子上就没派性。我母亲五十年代初期访问过程砚秋,第三天程砚秋就带着王吟秋到我们家“回拜”。王吟秋是当时这件事的见证人,他1995年在天津参加中国京剧节时,还特地跟我谈起这件往事。电视台采访他,让他谈谈自己对男旦的看法。他这样回答:“徐城北同志赞同男旦,你们采访他去吧,我以为:他的理由很充分。这问题由文化人谈,比找我们自己说自己更合适。”记得那一阵他私下也很表示出亲近感。每年过春节,都是他抢先给我打电话拜年。我说要到他双榆树的家里拜访,不知道什么原因,他硬是一次次地谢绝。我心暗想:男旦的家有什么不能看的东西么?我随后又听说,他在家里教女学生时,一定要拉一位不相干的男同志作陪。还有,不久前我还听一位“赵荣琛身边”的人传话,说赵老很羡慕世济身边有个徐城北,还说“要是想个法子让徐城北转到咱们这边,就好了”。
话还回到火丁身上,她很早就拜师赵荣琛,其中原因我不得其详,是她选的老师,还是老师选的她?但我听说到一则马路新闻:她一个小女子,唱起来却很有那种男旦的味。我听了想了一想,的确她还真有这么个特征。但光有这一点,如何把她与赵老联系起来,我还是不得其详。但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火丁大不幸的事:她的赵老师突然去世!这可是个大问题与大难关。现代程派“赵·王·李”这样“三驾马车”的结构平衡被突然打破。赵与王本是一路,唱戏依靠很深的功夫,但年岁上又多少有些“过气”;而世济正在最好的时期。赵之一旦去世,那天平只会更向着世济的位置倾斜。这个大结构暂时不提,且看她张火丁此际应该怎么办?一种,是转向王,也同样是男旦,与赵共同的地方多;但估计只能是名义师徒,王吟秋还有原来的徒弟呢!如果转向世济,那流言就会更多,或许被认为“人一走茶就凉”而“另攀高枝”呢。我多年游离于梨园的具体事物,但思想不懒惰,常常替别人担心,想一些情理上可能发生的事。
过了没几天,报纸上登出一则新闻:介绍张火丁到南京向新艳秋学戏。说火丁在宾馆租了两套房子,一套自住,另一套搬请著名的前辈坤旦新艳秋进来住。她们一老一小一起过了一星期,其间新艳秋教了火丁好几出程先生的戏。火丁也没有正式拜师,但是“面对面”真学了。首先,她南下之行的这火候“掐”得极好,其次这找人找得准。自己的恩师不在了,转投另外“两驾马车”肯定不行。干脆请出当年师爷的“劲敌”来教自己,而这“劲敌”深藏多年,肯定愿意在北京收自己这一个不在名义之内的小徒弟。我记起早在这时之前,北京举办过一场纪念程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盛大演出。就演一场,一出完整的《锁麟囊》,先后五个薛湘灵:上海李蔷华,北京李世济,随后是赵荣琛与王吟秋,最后一场的最后一小截,才是资格最老的新艳秋。我看了那场戏,座位在七排中间,是李世济给的票。因为这场阵容“过于强大”,所以戏票格外紧张。而他们五位主演,都能得到几张最佳的赠票。我事先知道世济肯定有票,但也没敢张嘴要徐城北简介,我知道她一定会给她最看重的朋友。让我大大意外的是,唐在昕(世济的丈夫)主动给我打了电话,说世济讲“要把最好的一张给城北”。我有些意外,我不过是从本院工作人员的角度,为她帮忙了几年,怎么她会把这样好的票给我呢?因为我知道在这场的前排座位中,会有许多与程派程家有渊源的人—他们会四处张望,看这前几排都来了什么人,每个人分别属于哪一方……许多人都会在开演之前发出这很微妙的一瞥。它是无言的,但又是有无形力量的。我甚至想到:世济之所以要把戏票送我,也就是希望周边的人,能发现徐城北这么一个“傍”过她的人,如今正襟危坐于最好的座位上。在梨园,“傍”角的人应该“一傍到底”,这应该是做人的准则。当然,解放前程师息影务农的时节,秋声社的戏班散了,多数助演都被拉到新艳秋那里,戏份儿开得很高,很多程之四梁四柱都成为新艳秋的骨干。也正由于这一笔,程与新二人一直到后来公开见面,也还是面和心不和的。当然,新艳秋本人并无责任,她只求唱戏,不求其他,没多久也就息影舞台。直到重新出山,在江苏戏曲学校担任京剧教师。老实说,这样安排她是有些屈才的……
咱们还说这场演出,前边几个薛湘灵里,数李世济最出风头,可往下边演去,几个旦角全都一般。也许存在这样的道理:是李世济抢到了“春秋亭”一折。在程派演员的合作中,谁演这折谁就光鲜得胜。但出奇的是,最后一场的后半截,又冒出来一位息影多年的新艳秋。北京的老程迷疯狂地欢迎她,我也是第一次开了眼。她一招一式都实在好,处处如同不费力,又处处用力在点子上!事隔多少年后的今天,我猜想张火丁是否当年也在台下看过那出戏,如果她有幸看过了,她此生就一定会记住了这位出神入化的老太太!反正我看完戏后遇到老唐,他笑吟吟问我:“今天最好的是谁?”我猜想他内心的潜台词一定是希望我能夸一夸世济,不料,我张嘴就说:“新艳秋最好,甚至比程砚秋本人都强!”这是良心话,干这行多年了,遇到这种节骨眼的地方,是不能张嘴说瞎话的!
我打听过,张火丁是个旗帜鲜明的人,习惯直话直说,心里有准主意。不久,我的“娘家”中国京剧院改革又出新面貌,一团于魁智团长,二团张建国团长,似乎还有一个三团,其中就包含了张火丁的程派艺术工作室,一共十来个人。仅几个主要配演辅佐,如小生宋小川等,班子颇硬,戏班事务统一由火丁之兄火千掌管。她出外巡回就是打个人牌,我看过她一出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这戏在越剧里是旗鼓相当的徐城北简介,小生必须也强。可同名京剧就她一人从头唱到尾。为什么她会这么办?似乎与她的流派有关。程派主要是主角个人“卖唱”,对边上的“四梁四柱”要求并不过高。前两年她带队去郑州演出,郑州有个很有名的文化讲座,就萌生了一个主意,要我与她联合搞一次讲座。因她本人演出前关闭了手机,我转而与她哥哥联系,未果。于是就错过了这次当面谈火丁的机会。今后呢?如有机会我倒还是很愿跟她一聊。
最近又听说她调入中国戏曲学院,在那儿教课并演出。不管是福是祸,反正她又进入自己艺术生涯的新阶段了。她应该比早期更成熟了。
[作者简介]
徐城北,1942年生于重庆,在北京长大,1965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。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,北京大学 *** 教授。已经出版各类著作九十余册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京剧文化和京城文化,著有《梅兰芳三部曲》、《老北京三部曲》、《老字号三部曲》及《中国京剧小史》等。